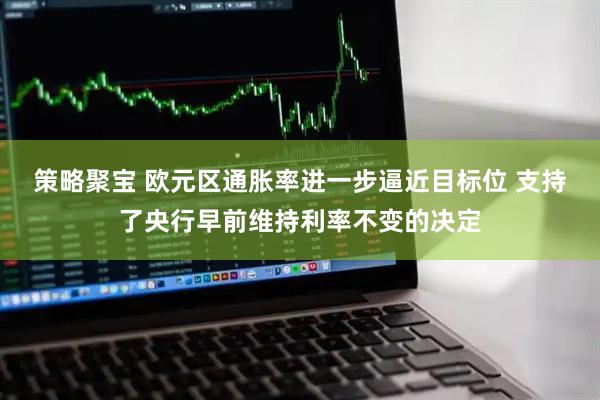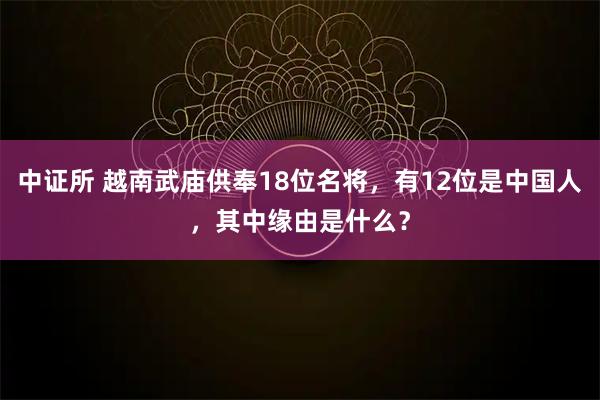大业证券
大业证券
由马来西亚导演张吉安执导,范冰冰领衔主演的电影《地母》(Mother Bhumi)近日正式发布预告片。
影片已入围第38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在第62届金马奖中获得包括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张吉安)、最佳女主角(范冰冰) 在内的8项提名,涵盖摄影、音效、造型等重要技术奖项 。
影片故事背景设定于1990年代末的马来西亚吉打地区。范冰冰饰演的华暹农妇“凤音”在经历丧夫之痛后,白天耕作,夜晚化身解降师为村民驱灾治病。当土地权益纠纷引发的异象逐渐逼近,她必须化身“大地之母”,在生死关头化解根植于土地中的殖民遗恨 。主演阵容还包括许恩怡、白润音与蔡宝珠 。
《地母》由马来西亚、意大利及中国香港联合制作,延续了张吉安导演融合民间信仰与历史现实的作者风格。
「导筒directube」张吉安导演专访回顾
2025 HKIFF INDUSTRY Project Market

「导筒directube 」于本周再度受邀探访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HAF)电影业办公室项目市场(HKIFF Industry Project Market),今年的入围项目包括多位得奖导演新作,其中包括马来西亚导演张吉安的新片《地母》(MOTHER BHUMI),该片再次聚焦东南亚边陲的民间叙事,延续《南巫》之后对族群历史与土地整治的深耕,同时融合了巫术、殖民记忆与女性抗争等话题的探讨,更是邀请到华人演员范冰冰加盟主演。
同时,本片为马来西亚与意大利、中国香港联合制作,在HAF制作中项目(WIP)推介会(Open Pitch)上的一段片花,更是引人注目,其中范冰冰的多场精彩戏份也是首次公开。





「导筒directube」前方记者在Project Market现场采访导演张吉安,带来关于该片的第一手报道。
专访正文
导筒:从《南巫》到《地母》,很多观众可能会期待这一次你带来的新作会呈现一个怎样的状态,是不是会是“惊悚”的一种风格。
张吉安:可能有一些中国的观众之前看过《南巫》,我在网络上是看到有中国观众说本来以为这是一部“恐怖片”或者“惊悚片”,但是看完以后觉得“看了个寂寞”、“完全不恐怖”、“不是很惊悚”,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邂逅。
我想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大家一路以来对于东南亚这种比较边界的,所谓的“奇幻题材”,都抱着一种“我们要看恐怖片”的态度,而且希望越猎奇、越惊悚、越恐怖越好。

张吉安《南巫》 (2020)
对于我来说,一方面是因为我生长在这个地方,那边的风土民情在外人看来是猎奇,可对我其实就是日常。所以我一路以来不管是写自己的故事还是拍电影,都不想用猎奇视角,而且选择日常的视角去诉说。
其实这边的真实生活是“百无聊赖”,没有太多让我觉得它可怕的地方,所以我在将故事转换成电影语言的时候,我反而是会用到很多人与人的日常交流,就算是在所谓的“异度空间”中也是一种“万物皆有灵”的视角去诉说故事。

张吉安导演在《南巫》拍摄现场大业证券
导筒:这种“猎奇”、“魔幻”的标签实际上是双面的。
张吉安:对,常常有一些影展会介绍“张吉安导演的作品是奇幻的”,可能过去的影展是想要将每一个导演都归类的,比如“写实”、“魔幻”、“东南亚奇幻风格”之类的,我也没有很抗拒,因为有时候“被分类”也是方便影展方面去宣传、推广、诠释你的作品。
导筒:你在不少的采访中提到曾经有过很多的田野调查。
张吉安:我在念完电影之后,没有马上拍电影,而是花了大概20年的时间,做了很多的民俗田调。所以我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是跟身边同一时期的导演不太一样的,我用一种人类学的方式去记录这些东西,加上当时对民俗方面非常感兴趣,所以就为自己未来的电影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故事资料馆”,慢慢的,随着我到处去收集口述故事,故事越收越多,资料越采集越多。

张吉安2016年为办吉打稻地节进行田野调查
张吉安:《地母》的故事来自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我小时候,家附近的一个村落中有一位女性巫师。我经常听到她的名字,她之所以有名气也是因为她是那边唯一的一位女性巫师。现实情况是,男巫师比较多,很巧,我第一部片子叫《南巫》,不是“男巫”,不是性别上的指向。
那时候地方上经常会发生一些所谓的土地的纷争,也造就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当仇恨产生了,他们就会用“降头”来互相伤害,互相给彼此一种警告——“你要把土地还给我”。当时正是这个女性巫师负责去解救这些中“降头”的女性,但后来她就消失了,有人说她死了。

桂治洪《蛊》(1981) 截帧
再后来,当我长大念完电影回到家乡做田调,开始走访村落的时候,有老人家再次提起这位女巫,说当时她得罪了一个地主,可能是惹到了某个势力就躲到了森林里去了,当然,也有人说他在斗法的时候受伤了,躲到森林不见了。
当时我就回忆起来了这位女子,我觉得大家对她,对这位女性身上的乡野传说感到很有趣——她是一个真实的人,用斗法的方式来对抗一些所谓的男巫师,或者是当时所谓的一些盘踞的男权势力,虽然她消失了,但她的传闻一直还在,大家没有忘记她。
我也告诉我自己,有一天我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并且重新书写这个故事,结果就在疫情的两年时间里,在家里闲着的时候一口气把剧本写了出来。

导筒:所以这个剧本其实蛮早就已经写出来了。
张吉安:当然,这个剧本其实早在2020年左右就写了,我的生活就是一有空就写剧本,除了拍片没有其他事情做。所以到现在为止,我的电影项目的“序列”已经排到了第十个,剧本写到了差不多第七个,拍的话,是第四部。
导筒:非常规律的一种创作习惯。那后来是如何与范冰冰接触并且选择她作为主角,她作为演员有哪些地方打动你?
张吉安:当时2023年圣诞节前夕,范冰冰刚好去参加第34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她在电影节期间看了我的作品,然后她那边就来打招呼问能不能约见一下。其实在这之前,我对她并不是很熟悉,也没见过,只知道她是一位女演员。

范冰冰与导演张吉安在第34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
一见面,我听她谈对我作品的看法,我觉得她讲得蛮有意思的,她说她从来没有拍过这种东南亚式的作品,几乎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题材,而且东南亚题材的作品氛围对她来说很陌生的,随后她就问我接下来有什么剧本想要拍的,我就讲了几个故事大业证券,《地母》就是其中一个,她听完第一句话就是:“能把这个剧本留给我吗?”

导演张吉安与范冰冰在勘景
其实我当时还蛮很直截了当,或者斩钉截铁的回答——我说我很少跟有明星光环的演员合作,我说“你很漂亮,但是我的《地母》要求演员不能够太漂亮”。我想要的这位女性的样子可能比较边界一点,有点像东南亚的女子,因为范冰冰的皮肤很白,可能生活中看上去不太像。
我记得她告诉我说:“我作为演员走红毯的时候,我的专业要求我把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大家,可如果我是在拍电影的时候,你可以把我当「垃圾」来看待我都OK。”
我听了这番话之后,我立刻明白她想要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角色,我当时就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合作的话,我把你的脸「摧毁」可以吗?所谓的「摧毁」就是把你的你的整个形象状态都摧毁,可以吗?”
她立刻说了四个字,我真的印象深刻,她说“奉陪到底”。我觉得OK,其实就是那一次见面之后,她的经纪人就一直在跟我们保持联络,所以后来的合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地母》开机照
导筒:你对范冰冰之前的银幕形象了解多吗?
张吉安:跟范冰冰合作的前提是我本身看过她的作品,但都是电影,我很少看电视剧,所以我没有看过《武媚娘》,看关于她的电影先是《苹果》,然后是《观音山》《我不是潘金莲》,其实主要是这三部。
之后因为我想要和她合作,所以我又去重看了这几部电影,但其实后来我又想到,就算我重看也对我自己的创作没有很大帮助,因为《地母》和之前她所演艺的故事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后来我们回到了我最开始跟她提到过的状态,在准备这个角色的时候,“摧毁”她的形象,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我们整个的筹备过程是很保密的,主要是因为我想让范冰冰可以非常安静地进入这个地域。

《我不是潘金莲》 (2016)
导筒:虽然《我不是潘金莲》中也有一个妇女形象,但相对是比较传统的中国妇女的形象。
张吉安:对,《地母》对她而言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当时带她去体验生活,真的是去到了边界的稻田边住下,每天早上6点起身以后,花两个小时下田,不光是体验,我还记得我们养了一头水牛,还有一些其他的动物,是真正感受稻田人家的生活。
因为我本人就是在稻田边长大,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每天有机会去稻田里走一走、踩一踩,她是感觉到什么叫做泥土,加上“地母”不光是寓意着一个神明,还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所以我希望她能够踩在这个马来西亚跟泰国的边界的泥土之上,这种质感是不一样的,也是我想要的。

导筒:其实这一次的语言有华语、闽南语、马来语、泰语等多种语系的交织,而且这对于演员、对于导演来说应该是不小的挑战。
张吉安:很多的中国演员能来到亚洲的其他地区,通常都会说华语,或者是饰演的角色本身就是中国人。但这一次我跟范冰冰说,你不能够还演中国人,在《地母》中,你要演一个马来西亚人,而且还要是暹罗人和华人的血统,所以语言是我必须要考量的。
因为我本身是做语言研究的,所以我确实可以说我很刁难,我要求范冰冰必须要学当地的马来话、暹罗话,包括福建话等等,其实前前后后花了大概三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语言的筹备和适应工作。

导演张吉安表示这一次为了拍摄《地亩》,专门租了几亩田地,3个月内从种稻到收割,还将田中废旧的老木屋重新修建。
张吉安:当时她住在香港,我们就通过视讯的方式,每两天我们同步一次,哪怕是一句对白、两句对白,我们都要花个一个小时。可能几个星期时间都是在让她知道某个字地道的念法是怎样,代表的内容是什么。
我不敢说范冰冰是100分,可在我们给到很多熟悉这些语言的人听之后,他们都觉得OK,绝对是过关的。也有人跟我提过要不要后期配音,但是从我的角度,台词、语言这件事是坚决不能用配音的,所以我觉得她非常不容易,在我的要求下很好的学习掌握了这些语言。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一次的合作是蛮愉快的。
导筒:除了语言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些合作细节?
张吉安:因为因为戏里边的故事,那些日常的生活我都非常熟悉,她做的任何一件事,比方说女性在外面耕田、在厨房干活,或者是开着摩托车从田埂里经过,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和她一起讨论,然后她一件件亲自上阵,没有任何替身,按照我们说的这种非常在地的生活方式来呈现的。
导筒:从片花呈现的质感来说,可以说是延续了您之前作品的一些气质,无论是东南亚的这种历史往事,亦或是民间的传说,而且比起《南巫》可能在某种层次上更加的丰富。
张吉安:我和我的制片黄巧顺从《五月雪》到现在一直有合作,而且我们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创作方向是属于非商业类型。我们的电影实际上有一个很强烈的主题,就是在探讨华人在东南亚的这种离散,包括他们的在地,还有对土地的认同。你所说的历史往事,在我看来,不止是一些历史事件遗留下来的伤痕。

《地母》这部电影中探讨了曾经的殖民问题,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曾经是属于泰国,暹罗皇朝在1909年跟英殖民就签署了一份《曼谷条约》,叫《1909曼谷条约》(Bangkok Treaty of 1909),这片土地就割让给英国了,所以基本上其实我住的那地方是非常典型的,被交易来,交易去的一种状态。这片土地也因为同时有暹罗王朝和英国的不同文化同时存在,而呈现出一种丰富的样态,现在看来,这些殖民色彩,还包含了某种伤痕和遗恨,那些东西还存留在这片土地上。
所以如果是和《南巫》相比较,《地母》探讨更深入的还是人与土地之间的守护、纠结和争夺。《地母》中是凤英这个角色她仿佛就是一个大地的母亲一样,一直在这片土地上,思考着田埂上面的生活的人、她死去的丈夫,她的闺蜜、她的邻居,对面同姓氏的村庄中的人们的遭遇,她好像是觉得有点无能为力。
导筒:除了片花,可以看到这张释出的海报是很有一些深意的。
张吉安:其实海报中有两颗树,有一颗是秃顶枯萎的,这象征凤英的老公,是一个逝去的生命,但是她依旧选择守护在这种有生命和无生命之间。她所处的位置,正好是马来西亚,对面是泰国。她透过手上的“地亩”神像来思考自己该何去何从。她站在自己的土地上,但是对岸是曾经的故乡,她在这种抉择之间徘徊,也在寻找内心深处的答案。

张吉安《地母》 剧照
导筒:“地母”这样一个神明在现在,你是怎样看待的?
张吉安:拍很多时候拍关于东南亚或拍民俗题材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认为神明在某一刻会出现。但其实在我的电影里,我会想把人类学的一种东西放在对信仰的思考当中,它不是表面看起来光怪陆离或者是惊悚的、所谓的奇幻的状态,其实代表着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投射。
有的时候,你信仰某个“真神”,其实你是把所有的寄望投射在Ta身上,你就把Ta当成某种为你实现目标、实现愿望与期许的东西。
也许是因为我长期都在做田调,我父亲和家人都和民族信仰有关,所以我常常就会跳脱出来,而不是以单纯的信仰去看待他们,是人对于自然界人对于万物有灵的这种敬仰,甚至是一种敬畏,再结合在地的一些历史背景去看待时,反而是更加契合。
导筒haf2025系列推文:
创作不易,感谢支持
融易富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